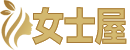股東訴訟另一股東侵占財產(chǎn)罪(股東訴訟另一股東侵占財產(chǎn)罪管轄法院)
最穩(wěn)當?shù)耐顿Y,莫過于既能在企業(yè)收益巨大的情況下當股東,可以享受巨額的股權(quán)回報;又能在企業(yè)虧損的情況下當債權(quán)人,可以讓投出的本金保本收息。“明股實債”就是這樣一種“必贏”的投資方式。
“明股實債”的“投資人”,在向企業(yè)注資時,會與企業(yè)簽訂《投資協(xié)議》。這樣的投資協(xié)議不管條款如何花哨,最后落實如何回款這一條,會強調(diào)企業(yè)虧損或盈利后,企業(yè)某股東或企業(yè)本身要履行回購義務,最終的回購額算下來,能夠做到“保本付息”。
實踐中,不少涉嫌挪用公司資金、職務侵占的當事人,是公司的唯一真實股東,公司的其他股東,往往都是“雞賊”的“明股實債”債權(quán)人。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司法實踐中,一人公司的唯一股東,涉嫌挪用資金、職務侵占罪,還是有很大出罪空間的。
最高法判例:“明股實債”股東實際上是債權(quán)人,不具有股東地位
實踐中,“明股實債”的投資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一段時間以來,民事法庭上,可謂判什么的都有,有的法院認定為債權(quán)人,而有的法院也會認定為股東。
2023年3月1日,最高法在再審案件《黑龍江事益科技發(fā)展有限公司、付麗華借款合同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jiān)督民事裁定書》(2023)最高法民申7050號,正確的提出“《投資合作協(xié)議》的約定不具有共同經(jīng)營、共享收益、共擔風險的投資合作特征。事益公司工商登記雖變更付麗華為公司股東,但付麗華不參與事益公司的經(jīng)營管理,其投入的資金不承擔任何經(jīng)營風險,只收取固定數(shù)額的收益,該1300萬元名為投資,實為借款。僅就事益公司與付麗華雙方之間的法律關系而言,為民間借貸性質(zhì)”。
真實的股東,是要以出資額為限,對公司的盈虧承擔責任的。如果公司虧損了,是不可能回本的。只有借款或者存款,在法律上才能切實保本付息。顯然這樣的約定,從本質(zhì)上是保本付息的借款(債權(quán)投資),而不是盈虧自負的股權(quán)投資。最高法上述判例無論從法理上,還是從實際保護公司、合伙企業(yè)等投資、借款制度上,都是妥帖的。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統(tǒng)一法律適用工作實施辦法》,該辦法明確規(guī)定各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決必須與最高法類案類判。在最高法已經(jīng)在這一問題上有了類案的情況下,司法中的亂象就此打住,以此案例為準,不認為“明股實債”方具有股東或者合伙人地位。
一人公司的股東,不是挪用資金、職務侵占犯罪的主體,不構(gòu)成上述兩罪
在抽絲剝繭縷清公司股東脈絡,真實股東只有一人,其他股東均是“明股實債”的債權(quán)人的情況下,即便“債權(quán)人”登記為了股東,這樣的股東地位原本也不應當被法律認可,這樣的公司理所當然就是法律上的一人公司。在真實股東只有一人,涉嫌挪用公司資金或職務侵占的案件中,刑法學界和司法實踐主張不構(gòu)成挪用資金、職務侵占的觀點更為主流。
在學界,以張明楷教授為代表,提出一人公司的股東不應當構(gòu)成挪用資金、職務侵占犯罪。
張明楷教授在教科書中寫道“一人公司股東將公司財產(chǎn)據(jù)為己有的,則不宜認定為職務侵占罪。因為從實質(zhì)上看,一人股東沒有侵害他人財產(chǎn),沒有給他人(包括其他單位)造成財產(chǎn)損失。倘若一人股東通過將公司財產(chǎn)據(jù)為己有的方式逃避債務等,則只能以其他犯罪(如詐騙罪等)論處。因為職務侵占罪所保護的是本單位的財產(chǎn),而沒有將其他單位或者個人的財產(chǎn)作為保護對象”(《刑法學》第六版第1337頁)。“在一人公司中或個人獨資企業(yè)中,股東或者投資人挪用資金的,不成立挪用資金罪”(《刑法學》第六版第1341頁)。
在最高檢層面,曾經(jīng)在《檢察日報》和最高檢的各大公號公布了一篇《一人公司股東攤上事兒》的紀實文章,詳細闡明為何承辦人和最高檢專家都認為一人公司股東不能犯挪用資金、職務侵占罪的理由。
該案案情為:2023年4月,宋某在武漢注冊成立珠翠(化名)首飾有限公司(下稱“珠翠公司”),主要經(jīng)營貴金屬批發(fā)與零售。宋某是唯一自然人股東,也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100%。公司成立后并未設立對公賬戶,一直以宋某個人的銀行卡作為公司資金往來賬戶。
之后,宋某開始炒黃金、鉑金等盈利性期貨,由于個人賬戶與公司賬戶混同,他多次將公司資金挪作私用。疫情期間,市場價格波動,宋某購買的期貨虧損嚴重,公司資金鏈也隨之斷裂。
“承辦人查閱了大量相關案例、司法解釋,卻始終找不到一個明確的答案。為了準確定性,胡繼宗依慣例打開檢察機關的“智庫”檢答網(wǎng)尋求業(yè)務指導,得到三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涉嫌犯罪。第二種認為當一人公司股東與公司資產(chǎn)混同時,公司的企業(yè)法人被否定,公司不再獨立承擔債務,股東需對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此時便不涉嫌挪用資金罪;但如果股東與公司資產(chǎn)獨立,公司屬于企業(yè)法人,則一人公司股東挪用公司資金涉嫌犯罪。第三種觀點則認為,挪用公司資金實際侵害的是股東的利益,而一人公司股東挪用公司資金不存在侵害其他股東利益的情況,自然不涉嫌挪用資金罪。
基于對相關法條的理解及對案件事實的認定,胡繼宗個人更傾向于第三種意見。之后,他擴大范圍繼續(xù)搜索,發(fā)現(xiàn)最高檢專家組曾作出過‘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職務侵占公司財產(chǎn)的行為不宜認定為職務侵占罪’的解答時,頓時眼前一亮。”
“雖然罪名不同,但職務侵占罪和挪用資金罪侵犯的客體是一致的,都是公司的財產(chǎn)權(quán)利,本質(zhì)上是全體股東的財產(chǎn)權(quán)利。”胡繼宗解釋道,“檢答網(wǎng)的解釋明確,‘不宜把職務侵占罪的危害外延擴大為損害了外部債權(quán)人的利益,在個人財產(chǎn)與公司財產(chǎn)嚴重混同的情況下,一人公司股東處分公司財產(chǎn)的行為,因為不存在侵害股東利益的情形和危害,不宜認定職務侵占罪’。該解釋是基于對職務侵占罪侵害客體的準確理解,其背后的法理與邏輯亦可作為承辦人認定本案罪與非罪的參考。”
據(jù)筆者了解,在當前各地司法實踐混亂的情況下,上述最高檢刊發(fā)的這篇紀實報道是兩高層面釋放出的最權(quán)威的解答:最高檢內(nèi)部的“智庫檢答網(wǎng)”內(nèi)部,有最高檢內(nèi)部專家組做出過這樣的解答。在當前司法解釋對此沒有明確、指導案例也匱乏的情況下,讓我們明確了解了最高檢內(nèi)部的權(quán)威認識。
挪用資金也好、職務侵占也罷,都規(guī)定在侵害財產(chǎn)罪的類罪下。尤其是一人公司的股東與公司財務嚴重混同的情況下,股東是要為公司的債務負連帶責任的。一個股東從公司使用錢款,既不會侵害其他股東的利益、也不會侵害債權(quán)人的利益,顯然這樣的行為喪失了法益侵害性,也就不應當按照犯罪處理。
不按照犯罪處理也符合當前對民營企業(yè)家的刑事政策
當下,在全球疫情肆虐的背景下,保經(jīng)濟就意味著保穩(wěn)定,保市場主體才能保經(jīng)濟,保民營企業(yè)家才能保市場。早在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依法平等保護民營企業(yè)家人身財產(chǎn)安全十大典型案例之五:《麥贊新職務侵占、挪用資金無罪案》
最高法針對該些犯罪提出的刑事政策為:“嚴格把握民事糾紛與犯罪界限,依法保護企業(yè)家人身自由權(quán)利。公司合伙人之間的經(jīng)濟利益之爭,可以通過和解、調(diào)解及民事訴訟等方式來解決,正常的民事糾紛不應被作為犯罪處理。 刑事司法應牢固樹立謙抑、文明等理念,刑法介入經(jīng)濟活動應謹守最后手段性的原則,切實依法維護企業(yè)家人身安全,為經(jīng)濟健康發(fā)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務和保障。”
入罪舉重以明輕,哪怕有公司有其他股東或者企業(yè)有其他合伙人,行為侵害了其他股東或合伙人的利益,在可以通過民事途徑解決的情況下不作犯罪處理。更何況一人公司股東不可能侵害其他股東利益,和債權(quán)人的紛爭更可以通過民事途徑解決,更有不按照犯罪處理的必要性。
聲明:本站所有文章資源內(nèi)容,如無特殊說明或標注,均為采集網(wǎng)絡資源。如若本站內(nèi)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權(quán)益,可聯(lián)系本站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