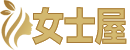精神衛(wèi)生法有哪些規(guī)定(精神衛(wèi)生法哪些內(nèi)容體現(xiàn)了預防原則)
精神障礙患者的救助與保護一直是社會的熱點話題。
從2023年開始,就不斷有人大代表在兩會上提出精神障礙患者的救助與管理問題的建議。2023年3月6日,全國人大代表、重慶涪陵區(qū)南沱鎮(zhèn)睦和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劉家奇在兩會上提交了《關于加大對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服務管理工作力度的建議》。
根據(jù)中國疾病控制中心2009年公布的數(shù)據(jù),我國各類精神障礙患者人數(shù)在1億人以上,然而公眾對精神疾病的知曉率不足5成,治療率甚至更低。
與龐大的患病人群形成對比的,是對這群人普遍的偏見和不同程度的歧視。
嚴重精神障礙患者
21歲時,生活在福建某縣城的徐國忠被確診為急性偏執(zhí)型精神分裂。32年來,徐國忠5次復發(fā),有幾次住進精神病院。有一次因為沒錢,他遵醫(yī)囑把自己關在家里,在家人照顧下吃藥,兩個月后也能逐漸清醒過來。
他已經(jīng)習慣了同事、鄰居對他的躲避和背后的指指點點。有一次,他的工作單位舉辦歌唱比賽,他去報名卻被領導拉到旁邊,“他說,你不能參加,你萬一在演唱比賽期間出什么亂子怎么辦?“徐國忠對界面新聞說。
患病初期,醫(yī)生、家里人都勸慰他:不要想太多,好好休息。他也曾“在家里吃了睡、睡了吃”,渾渾噩噩地過了幾年后,他還是覺得“人生不能這樣。”
清醒的時候,徐國忠一直積極地希望自救。
他回到原先的單位,請求領導給他換了一個相對輕松的崗位。公司倒閉后,他又開了一家自己的打印店,但因為生意不錯、工作強度大,他再次病倒。第三次創(chuàng)業(yè),他選擇的仍然是開打印店,但這次他知道了,“患了這個病你不能夠再按正常人的工作強度來要求(自己),”他說,他每天接一定量業(yè)務,對于急活、重活一律不接,打印店運轉(zhuǎn)至今。
即便有一定的勞動能力和收入,徐國忠跟大部分精神障礙患者面臨一樣的困難——缺錢。從去年開始,他就嘗試申請“監(jiān)護人補貼”。他被認定為精神殘疾三級,如果他在一定時間內(nèi)未發(fā)生肇事肇禍行為,與他共同居住的監(jiān)護人就可以申領看護管理補貼。
與享受福利相對的是,他幾乎每天都要填表,記錄自己的健康狀況,監(jiān)護人要定期到社區(qū)報告他的身體狀況,“被列為了社區(qū)的重點監(jiān)控對象,上‘黑名單’了。”他說。
像徐國忠這樣的精神分裂患者被稱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2023年5月,衛(wèi)生健康委印發(fā)的《嚴重精神障礙管理治療工作規(guī)范(2023年版)》(以下簡稱“規(guī)范”)中將患精神分裂癥、分裂情感性障礙、偏執(zhí)性精神病、雙相(情感)障礙、癲癇所致精神障礙、精神發(fā)育遲滯伴發(fā)精神障礙六種精神疾病明確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
根據(jù)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解釋,嚴重精神障礙是指疾病癥狀嚴重,導致患者社會適應等功能嚴重損害、對自身健康狀況或者客觀現(xiàn)實不能完整認識,或者不能處理自身事務的精神障礙。但因為”醫(yī)學上很難用病情去判斷這個(嚴重與否)。所以在操作上其實是直接認定這六種。” 公益法律機構(gòu)深圳衡平機構(gòu)發(fā)起人、精神障礙權(quán)益倡導領域知名律師黃雪濤介紹。
黃雪濤認為,這樣的分類是不合理的,“它使用了一個群體性的標簽,讓執(zhí)法的范圍擴大化了。”
根據(jù)《民法典》的規(guī)定,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成年人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盡管將一位成年人宣告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所需要履行的程序已經(jīng)規(guī)定在《民事訴訟法》中,但是在實踐中,行為能力宣告制度并未得到嚴格的執(zhí)行,而是逐漸形成了凡是被送進精神病院的(疑似)精神障礙者,均被醫(yī)療機構(gòu)視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潛規(guī)則”,這種做法也常常得到司法機關的接受與承認。
而嚴重精神障礙的解釋中的“對自身健康狀況或者客觀現(xiàn)實不能完整認識,或者不能處理自身事務”,與《民法典》中的“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存在的微妙聯(lián)系,可能會強化對精神障礙患者民事權(quán)利的剝奪。“相當于醫(yī)學上一認定你患這六種病,然后所有有這種病史的人都可以定義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黃雪濤說,“這是法律術(shù)語被病理化的解讀了。”
規(guī)定與執(zhí)行的落差
2023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wèi)生法》開始施行。作為我國精神衛(wèi)生領域的首部法律,它從更加人性的角度關注了精神障礙患者的問題。比如,它明確了患者住院自愿的原則。
但是,《精神衛(wèi)生法》的執(zhí)行效果卻并不盡如人意。
2023年全國兩會上,農(nóng)工黨中央曾經(jīng)提交提案名為《關于全面貫徹實施,加強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救治救助管理的建議》。其中指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的管理涉及公安、民政、衛(wèi)生、社保等多個政府部門,但目前仍未建立完整的部門協(xié)調(diào)機制,再加上基本政府、機構(gòu)缺乏配套措施和資金來源,導致《精神衛(wèi)生法》一直未得到有效落實。
盡管《精神衛(wèi)生法》規(guī)定,精神障礙患者認為行政機關、醫(yī)療機構(gòu)或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侵害其合法權(quán)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訴訟。但是,在長期以來的司法實踐中,精神障礙患者想以自身名義,獨立、自主地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時,常常無法獲得司法救濟。
根據(jù)《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自然人可以作為民事訴訟的當事人。但同時,第57條規(guī)定:“無訴訟行為能力人由他的監(jiān)護人作為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
“作為一個精神病患者,他去告侵權(quán)一方,都離不開醫(yī)院的診斷。但去推翻醫(yī)院的這么一個診斷是非常困難的。”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公益律師廖建勛說,“從社會角度來講,很多人會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待精神障礙患者的陳述。一個曾經(jīng)的精神障礙患者老是說他沒病的時候,很多人還是會說他有病。”
廖建勛曾是某三甲醫(yī)院的醫(yī)生,2010年他轉(zhuǎn)行成為律師。10多年來,他辦理的精神障礙相關的案件大都是出院難,以及患者認為自己被強制送醫(yī)、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權(quán)益這兩類。
“雖然在《精神衛(wèi)生法》里邊有一些討論,但實際操作上變化不大。”黃雪濤說,她的衡平機構(gòu)收到最多精神障礙患者的委托就是關于難以離開精神病院的,“比如說出院這個問題。雖然《精神衛(wèi)生法》有了很多的出院的設置在里邊,但實際上我沒看到變化。”
廖建勛曾經(jīng)辦過一個案件,患者被家里人送到精神病醫(yī)院治療。“他認為自己好了,醫(yī)生也跟他說,他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穩(wěn)定了可以出院了。但是因為送他過來的家里人一直不肯接他出院,那么導致他就被迫一直待在醫(yī)院里面。”
在精神障礙患者的出院、入院問題上,多年來,精神病醫(yī)院有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誰送入院的,由誰來接出院。廖建勛分析,醫(yī)院主要是為了避免承擔符合出院標準的患者出院后肇事肇禍的法律責任。為此,他建議在《精神衛(wèi)生法》中強化對患者自愿出院的一些程序規(guī)定,尊重患者的自愿出院權(quán)利,以及免除醫(yī)院的一些相關責任。
另一方面,《精神衛(wèi)生法》中對精神障礙患者監(jiān)護人的監(jiān)護權(quán),做出了比較明確的規(guī)定。但因為沒有規(guī)定醫(yī)療機構(gòu)的審查機制,如果監(jiān)護人與患者存在利益沖突,醫(yī)療機構(gòu)采信這樣的監(jiān)護人的監(jiān)護意見,做出醫(yī)療決策,就極有可能損害患者的合法權(quán)益。
S市的jerome就經(jīng)歷了這樣一場沖突。2023年8月,與他離婚7個月但仍然住在他房子中的前妻打電話報警稱,“與前夫發(fā)生糾紛,感覺前夫精神異常,無需民警到場,自行去派出所求助民警”。
第二天,女兒的同學家長到派出所報案稱,jerome在網(wǎng)絡群內(nèi)發(fā)表了威脅學生的言論(前妻在法庭上曾提交相關QQ群聊天記錄,但法院最終對該證據(jù)的真實性未予采信)。隨后,2名民警、3名特保人員將正在家中洗澡的jerome送到區(qū)精神衛(wèi)生中心就醫(yī),隨行的還有前妻、以及居委會等相關社區(qū)人員。
當天,jerome被區(qū)精神衛(wèi)生中心確診為偏執(zhí)型精神分裂癥并入院,由于他的父母在外地,女兒還未成年,第二天,居委會主任為他補辦了住院手續(xù)。
Jerome在區(qū)精神衛(wèi)生中心住了3個月后,前妻為他辦理了出院手續(xù)。“因為我就只能說還是要好好過日子,還是要回去復婚什么的。該裝的時候還是得裝。” Jerome說。但2023年2月,前妻再次撥打110“稱老公有精神疾病,之前被民警帶去過醫(yī)院”。2023年3月8日,Jerome再次被民警送到市精神衛(wèi)生中心治療了3個月。
高昂藥費
李志強是中國精神殘疾人及親友協(xié)會的秘書長(以下簡稱“精協(xié)“),也是精神障礙患者家屬,他的哥哥患上精神分裂已經(jīng)52年。因為哥哥,他加入了精協(xié),18年來,他見過無數(shù)被精神障礙困擾的家庭。
“我一開會他們(家屬)就哇哇痛哭,各種訴苦訴怨。”李志強說,通過多年觀察,他認為復發(fā)是精神障礙患者和家庭最急需解決的問題。
高復發(fā)率是精神障礙的特征之一,“住院—回家—再次發(fā)病入院”,這個循環(huán)往復的過程被精神科醫(yī)生稱為“旋轉(zhuǎn)門”現(xiàn)象。李志強曾對全國范圍內(nèi)的10家精神病醫(yī)院做過調(diào)研,結(jié)果顯示,精神障礙患者的復發(fā)率普遍在60%以上,而多次復發(fā)的患者通常都需要終生服藥。
導致復發(fā)的因素很多,但部分或完全停藥是首要原因。李志強總結(jié),患者停藥的原因不外乎兩種:藥物副作用大、藥品價格高。
這兩點,徐國忠都深有體會。因為常年服藥,他的牙齒大部分都脫落了。發(fā)病服藥期間,他還會有翻白眼、流口水、發(fā)呆發(fā)愣等不可控制的生理反應。因為副作用大,也因為吃不起“兩三百塊錢一顆”的藥,他第一次出院后就停藥了,也很快復發(fā)了。
隨著2004年我國啟動“中央補助地方衛(wèi)生經(jīng)費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療項目“(簡稱“686項目”),對家庭經(jīng)濟困難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實施免費服藥、住院補助治療等救助。隨后,北京、上海、長沙等全國各地陸續(xù)出臺相關政策,為精神障礙患者提供免費服藥的救助,服藥難的問題已得到很大改善,但這對精神障礙患者來說遠遠不夠。
2023年1月,北京市人大代表、原首都醫(y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yī)院院長馬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精神障礙類疾病不僅影響患者本身健康,而且會對其家庭、社區(qū)乃至社會產(chǎn)生不良影響。”因此,她在北京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建議,將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納入長期護理保險范疇,將家屬照護服務及可穿戴設備納入支付范圍,以減少患者因病致貧、因病返貧。
“家庭的責任之大,精神障礙患者的家庭之艱難真的是外人真的很難想象。”律師黃雪濤認為,監(jiān)護人制度將精神障礙患者與監(jiān)護人權(quán)利、責任的深度綁定也是導致這些家庭貧困的一個原因。
“在理論上制度上定義了這些精神殘疾人是家庭的包袱。而且監(jiān)護人有責任不讓你這個包袱里的東西給社會添亂。”黃雪濤說,“但是,對精神殘疾人的權(quán)利保障是整個社會的責任。”
站在家屬和精協(xié)秘書長的立場,李志強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認為第一是聯(lián)合社會組織、政府力量建立精神康復學校。二是將精神障礙患者免費服藥寫入《精神衛(wèi)生法》,現(xiàn)在有的地方免費服藥了,有點地方還沒有,要讓各地制度統(tǒng)一起來。”
如何回歸社會?
精神障礙患者如何回歸社會一直是一道難解的題。
一方面,藥物反應帶來的生理疲憊、精神渙散,還有精神狀態(tài)上的抗壓能力較弱,都決定了精神障礙患者無法像正常人一樣承擔大多數(shù)的社會工作。但是目前在我國,并沒有專門為精神障礙患者提供的工作機會。
這些年來,在全國逐漸建起了一些“溫馨家園”、“陽光驛站”社區(qū)康復服務中心,可以為精神障礙患者提供過渡性地就業(yè)和社會化適應。但社區(qū)康復中心目前不僅未在全國范圍內(nèi)鋪開,而且它所能容納的患者有限,與龐大的患病群體遠遠不匹配。
而更難邁過的一道坎是社會歧視。
羅月紅是社區(qū)康復中心“長沙心翼精神康復所”的主管,此前,她曾經(jīng)在長沙市第三社會福利院(長沙市精神病醫(yī)院)從事了13年精神科臨床護理工作。
在精神病醫(yī)院工作的時候,她也會覺得自己受歧視。“我們那時候旁邊還有一個戒毒所,我們搭出租車去上班,大部分的人寧愿報到那個戒毒所,也不報到精神病院,怕被別人笑。”羅月紅說。
而對于Jerome,這種歧視是更具體可感的。出院之后,與他相識多年的同學曾經(jīng)特意關照過他:“你千萬不要說你進過精神病院,千萬千萬不要對任何人說。我們是熟悉,但是不熟悉的人,對你是會有敵意的。”
但即便是很熟悉的老朋友,也會在與他發(fā)生小爭執(zhí)時口不擇言。“他們會說,呦,那你今天吃藥了沒有?你是不是應該吃藥?又或者說,你剛才說這話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點過于激動了?有很多東西就是普通人和精神病人都可能會說、會做,但是一旦你(精神障礙患者)說了、做了,他們就認為這是發(fā)病的表現(xiàn)。” Jerome說。
精神障礙患者們也知道自己“不招人待見”。羅月紅說,長沙心翼精神康復所的精神障礙患者們都害怕見人、害怕被曝光,“要是你說明天到我們機構(gòu)來采訪,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他們,那第二天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不會來了。我們一些活動照片,比如說我提出要貼出來的時候,有些人就會說不要貼我的照片。我被別人看到(有精神障礙),就比較嚴重。”
徐國忠與他們感同身受。即便他今年50多了,他也不太在乎別人是否還歧視他,但是他還有孩子,“如果大家都知道了我有這個病,那對他也會造成很大影響。以后對他的婚姻、就業(yè)都會影響的。”
聲明:本站所有文章資源內(nèi)容,如無特殊說明或標注,均為采集網(wǎng)絡資源。如若本站內(nèi)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權(quán)益,可聯(lián)系本站刪除。